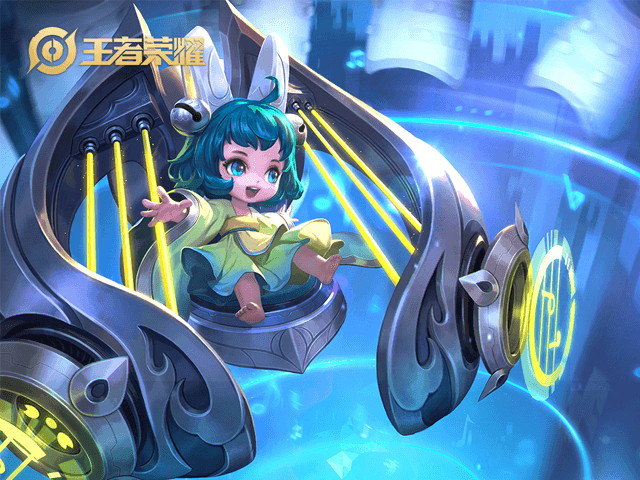美女野餐垫上的直播间美女直播平台名有哪些


岑梦凡
草叶尖儿扎得我脚底板痒痒的,像谁偷偷挠了根羽毛。2002年的太阳懒得很,瘫在天上吐热气,把塑胶野餐垫晒得暖烘烘的,一股子橡胶混着青草汁的怪味儿。妈把草莓酱抹得歪歪扭扭,面包片黏糊糊地扒着手指头,甜腻腻的香气钻进鼻子,倒让我想起昨天巷口小卖部玻璃罐里的水果硬糖。

“发什么呆呀?”爸举着傻瓜相机咔嚓乱按,镜头黑洞洞的,活像要把人吸进去。我忽然蹦起来,一脚踩翻果汁盒,橙黄色液体汩汩漫过格纹垫子,像打翻了老神仙的胭脂盒。“这是我的直播间!”我跺着脚喊,湿漉漉的脚趾在塑料布上打滑,“美女们都在这儿开播的!”——这话是偷听表姐打电话学来的,她总对着小镜子嘀咕“映客”“花椒”这些词儿,舌头卷得像含了颗冰糖。
妈噗嗤笑出声,揪了片槐树叶子贴我脑门:“哎哟,我们小美女主播,今天播什么呀?”风忽地把叶子掀飞了,绿影子打着旋儿跌进果汁滩,霎时染出琥珀色的边。我猛吸一口气,青草腥气混着果酸直冲喉咙,突然就想起舞蹈教室的木头地板味儿——上周刚摔过一跤,膝盖的淤青还泛着紫。
“播野餐!”我抓起半颗草莓按在腮帮上,凉沁沁的汁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爸的镜头追过来,阳光撞上塑料外壳炸开七彩光斑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几只麻雀从树影里窜出来,叽喳声碎得满地都是。我踮脚转了个圈,裙摆扫过草尖沾满露水,凉丝丝地贴着小腿。那一瞬间,野餐垫的胶味、草莓的酸气、草汁的绿腥,全拧成一股绳勒住腰,拽着我往亮晃晃的光圈里跌。
妈突然哼起歌来,调子软绵绵的,是那首她总在厨房唱的陕西小调。我跟着扭了两下,脚底黏着的草屑簌簌往下掉。爸的相机发出磁带卷带的嘶啦声,像有谁在很远的地方叹了口气。风掠过耳垂时,我听见表姐的声音从树梢上漏下来:“美女要笑,露八颗牙——”可槐树花正扑簌簌往下砸,细碎的白点子落进果汁里,像撒了一把小星星。
许多年后我站在真正的镁光灯下,睫毛膏被烤得发烫时,总会突然闻到塑胶垫的橡胶味。那些镜头黑洞洞的,依然像要把人吸进去。但再没人问我播什么,只有无数声音在喊:看这儿,笑,李艺彤看这儿!而我的脚尖总在细高跟上轻轻一捻,仿佛还能碾碎一颗2002年的草籽。
(远处有孩子追着风筝跑,棉线勒进掌心红痕蜿蜒如河。一只蒲公英突然炸开,绒毛乘着风扑上我的睫毛——像给这草台班子直播间,加了层毛茸茸的滤镜。)